陈美霖把采访地点约在重庆郊外一座山上的寺庙——寺庙里存放着她一双儿女的骨灰,她的女儿小雪去世时两岁半,儿子小洋只有一岁半。
陈美霖和她孩子的悲剧如今已传遍全网:2020年11月2日,小雪和小洋从南岸区的锦江华府15楼窗户坠楼身亡。坠楼时,孩子的父亲,也就是陈美霖的前夫张波光着一只脚冲下楼,跌坐在地,痛哭撞墙。
根据他的解释,这起事件是一个意外,姐姐小雪抱着弟弟在卧室窗边玩耍,不慎掉落。

事发后,锦江华府小区的许多高层住户纷纷加装了防护网(猪儿虫 摄)
但后来赶到现场和医院的陈美霖和孩子外婆都发现了疑点,一是孩子胆子小,在家从不敢爬窗台;二是小雪身高不到一米,窗户护栏接近一米二,她不可能抱起弟弟翻越窗栏;三是事件发生时,张波到底在干什么,他对陈美霖的说法是吃感冒药睡着了,对朋友的解释却是在客厅吃外卖。
10天后,张波和女友叶诚尘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批捕。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叶诚尘多次向张波表示,如果张波有小孩,就不可能继续交往。2020年2月开始,两人多次共谋将小雪和小洋杀害,最终,张波将孩子从陈美霖处接来,趁着家中没有其他人,将正在次卧玩耍的两个孩子双腿抱住,从15楼窗户扔下。
婚姻

“判了吗?”当陈美霖出现在寺庙时,庙里的师傅问。
“还没有,再等等。”陈美霖熟练地回答,朝对方微微弯腰点头。
她已经记不清是多少次这样回答。自2021年7月,案子提起公诉后,常常有人到陈美霖的社交账号下方留言询问判决情况。

观音殿内,两个孩子的骨灰盒放在最底层。陈美霖看完孩子,起身后抹了抹眼泪(猪儿虫 摄)
这起人伦悲剧已经成为重庆城内的一桩公案。 7月26日,案子开庭那天,许多市民自发聚集在法院外等待结果,既表达对这位母亲的同情,也表达对审判席上那对“情侣”的愤怒。
但这些关注并不能减轻陈美霖的痛苦。孩子去世快一年了,陈美霖还会梦到他们。有时候,他们面无表情地站在床边,喊“妈妈,我们要走了”;有时候,她躺在床上,看到孩子们背对着自己坐在窗台边。陈美霖大叫着他们的名字扑过去,然后惊醒,黑暗的房间空荡荡的。
她接过师傅递过来的一把香,点燃供上,转身走进观音殿。两三米高的墙面上存满了骨灰盒,两个孩子的盒子放在最底层。寺庙里的师傅说,孩子“年纪小,冤屈太重”,只能放在最低处。
这个位置是陈美霖精心挑选过的,正对着殿前的观音像。她默默蹲下身,不说话,只是用手来回擦拭孩子的骨灰盒,又在观音像前跪下,祈祷了一分钟。等站起身转过头,黑色口罩的边缘有了明显被眼泪浸湿的痕迹。

寺庙在山顶上,一大片乌云低沉地压着,陈美霖在庙外上香祭奠(猪儿虫 摄)
她只有在家以外的地方才敢流眼泪。过去近一年,这个失去孩子的家庭,每个人都在心照不宣地守着一条看不见的界线。父母从不谈起小雪和小洋,有时,陈美霖回家早,妈妈就催她出门,“你别待在家里好吗?你出去玩,去哪里都行”。
陈美霖也不愿意把记者约在家里见面,“怕爸妈又想到这些事情,难过。”她朋友圈发布的照片,都化着精致妆容,在练习画画、插花,似乎生活得丰富多彩,看不到悲剧的暗影。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陈美霖定下的一家茶餐厅里,朋友陪着她同来。三人坐在桌前,陈美霖总是笑着答话,不回避任何孩子生前的细节。说到儿子贪嘴时,她还笑出声来,让人恍惚间觉得,两个小孩还在家里等着妈妈把零食带回去。
饭局尾声,朋友起身到包间外接电话,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人。陈美霖继续说着孩子生前的趣事,但很快,她的声音就哽咽了,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很多人都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我不会去的。我不想和陌生人聊起弟弟妹妹,然后忘记他们”。

陈美霖是重庆城里人,母亲退休前在一家大型汽车公司从事研发工作,父亲则是国企的后勤管理人员。作为家中的独生女,陈美霖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从小“除了下棋没学过,其他所有的特长班全都报过一遍”。
大专毕业后,她先去一家幼儿园当了几年老师,虽然工资不高,但自己“喜欢陪小孩子们玩”,幼儿园的工作环境也单纯。 在转行到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前,她的生活如顺水行舟,没有遭遇多少困境,性格也同样温和。无论是选定见面的时间地点,或是点一道菜之后,她总会轻声询问一句:“这样可以吗?”
如果非要说遇到的挑战,转行进小额贷款公司大概算一个。2017年初,陈美霖入职小额贷款公司时,接替的刚好是张波的岗位。
她对这个从未涉足的行业一窍不通,张波刚跳槽去了别的公司,但很热心地提供帮助。甚至有段时间每天下午在新公司打完卡后,再偷跑回旧公司,搬张小凳子坐在陈美霖身边,教她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业务,如何联系客户、审核资料。临近下班时,再赶回自己的新公司打卡,然后折回来接陈美霖下班,送她回家。
这是恋情的开始——一个乖巧、温和的城市女孩,遇上一个热心、能干的郊区青年。张波来自重庆郊区的农村,1994年出生,比陈美霖小三岁,却表现出了超出年龄的成熟体贴。他坚持每天接送陈美霖上下班,交往三个多月后,就把工资卡交给陈美霖保管。
更重要的是,张波帮助陈美霖的同时,自己也没有落下业绩,常常会在下班后继续跑客户,忙到深夜。“我觉得他上进、踏实。”陈美霖对本刊记者说,“我很信任他,他的眼里也只有我。”
但在朋友和父母的眼里,张波却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对象。 他只有小学学历,身高一米八三,体重120斤,太过瘦削,还爱穿花衬衫和紧身裤,陈美霖的许多朋友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土”。家里也没多少积蓄,父母早年都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后来父亲得了癌症,因为治病借了不少外债,去世时给他留下一套锦江华府约80平方米的小两居,贷款还没还清。

《新结婚时代》剧照
两人谈恋爱半年后,陈美霖意外怀孕了。 那时,她已经调到公司的行政岗位,每天都要加班,一个月出差四五次。
领导得知后找陈美霖谈话,“他说现在正是事业发展的关键点,孩子以后还能再要,如果放弃事业的话,可能要从头再来”。陈美霖对本刊记者回忆,领导同时暗示她,如果要生孩子,最好主动离职。工作、怀孕、家庭……陈美霖没有同时经受过这么多种压力,情绪很差,一回家就关在房间里哭。不过,张波的话打动了她,“他摸着我的头发说,别怕,你想要孩子就生下来,其他的我都会负责”。
生活的水流看起来顺理成章地流向了相信这个男人,和他结婚。陈美霖辞去工作,准备和张波的婚事——这是她“唯一一次对父母叛逆”。 她收了张波家里给的1000元彩礼,并自己出钱买了一对结婚戒指。父母虽然对这桩婚事不满意,但也很快接受了独生女的“叛逆”,承担了两人的婚宴费用。
2017年8月,这对认识半年多的年轻人结婚了。2018年3月,女儿小雪出生。
乡村

一审法庭上,张波大多数时候低着头。因为隔着防护服和面罩,陈美霖看不到他的表情,只是确定他始终没有抬头看向自己的方向。 当公诉人指控他把两个孩子从15楼扔下时,他只是“嗯,嗯”地承认了。
这个27岁的年轻人,从16岁左右离开村庄,一心想在城市里追寻远大前程,没想到汲汲营营10年后,终点却在这里。
张波的老家是重庆长寿区葛兰镇冯庄村,离重庆主城区近100公里,离长寿区城中心也有将近20公里。汽车一路向北驶出城区后,两侧的山渐渐多了起来,离村庄越近,道路也弯弯绕绕得越厉害。 开车的司机就是葛兰镇本地人,跑了十几年车,他告诉本刊记者,“十几年前,村子还没铺公路,得颠簸大半天。除非是要收班回家了,否则没人愿意跑这趟”。

《我和我的家乡》剧照
公路从村子边缘穿过,路边有一排五层的商品房。这是村里唯一的商品房,朝南,八九十平方米的面积,“一套房十几万元”。但更多的是新建的二三层小楼房——相比商品房,人们更习惯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起一栋独门独户的小楼。
不过,新公路和新房子都没能让村子显得更热闹。 本刊记者到达冯庄村那天是下午两点,乡道上几乎没有人,只有摩托车偶尔从没有硬化的路面上驶过,留下渐渐远去的轰鸣声。
村里人最多的地方是一家小卖铺,五六位上了年纪的村民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聊天。他们早听说了张波的事情,但对于有记者特地从北京来到村子,还是感到惊讶。一位大叔用口音浓重的重庆方言告诉其他老人,“手机都能看得到,全国都知道啦”。他今年55岁,在村子里算“年轻人”,会用智能手机和外界联系。至于真正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不期而遇的夏天》剧照
张波是离开村庄的年轻人中的一位。即便在这个交通不便的村子里,他家的条件也不算好,住的那栋砖木结构的二层老房子,“比人的年纪都大”。
早些年,父亲就去外面工地,做砌砖、泥水匠的活儿。母亲是个身形高大、爱打麻将的女人,有时候也跟着丈夫去工地干活,留下张波和一个姐姐在家。两个孩子都没读太多书,姐姐没上高中,张波在村里的中学只念了一两年——这是冯庄村近20来年的村庄常态,父母跟着工程跑,孩子在村里“放养”。

去建筑工地干活,曾是长寿区许多村民进城最常选择的差事。 相比其他行当报酬更高,如果懂架子工、瓦工、木工等技术活儿,每天能有300块工资,人手紧缺时甚至能达到500元。脑子更活络的,甚至还能攒起自己的队伍和人脉,拿到小工程。
今年42岁的汪涛就是从建筑工地起家的。他告诉本刊记者,2000年左右,自己刚进建筑行业那会儿,村里几乎所有同辈的男性进城都是去工地干活。“村里穷,去城里造房子比种地赚得多,一个带一个地去,相互学一学手艺。”他跟着家里做涂刷工的三叔去了市区,一开始只能做工资最低的力工,推小车、筛沙子,所有零活都干。空闲时,自己就抓紧学涂刷,慢慢才开始做技术活,如今是一名收入颇丰厚的小包工头,常年在重庆各个区县承包工程。

但有运气和能力像汪涛那样从工地上“突围”的农村人还是少数。大部分人只能辗转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间,做一天工得一天钱,维持生活。 在冯庄村人眼里,建筑工地是进入城市最便捷、最理所当然的跳板,但不算是体面的进城方式。在烈日或严寒下挑鹅卵石、运沙子、铲混凝土,不过是换了一个地点的面朝黄土背朝天,肉体上不轻松,精神上也得不到尊重。
真正的进城,得像城里人那样干净体面地生活。他们习惯把工地、工厂里的工作称为“打工”,把写字楼里的工作称为“上班”。如果能穿着西装皮鞋进出写字楼,成为“上班族”,才是老家人眼里高人一等的工作。
张波也有过短暂的工地生活。初中辍学后,他跟随父亲去了工地,但几个月后就离开了。他不是一个甘心“打工”的人。
观音桥
观音桥是重庆最繁华的商圈之一,从早到晚人头攒动。天色越暗,街道就越热闹。夕阳西沉的某个时刻,在写字楼里待了整个白天的“上班族”们被打卡机释放出来,走上招牌鳞次栉比的步行街。街道两侧的霓虹灯已经亮起,把路面照得缤纷透亮。游客早早来到音乐喷泉旁,才能在喷泉从夜色中拔地而起时抢得一个观赏的好位置。
稍远处高耸的写字楼,在夜幕下成为一面面巨大的广告墙,姹紫嫣红的灯光在楼体上变换出各种商品画面。 张波就职的公司就在其中,一座分布着十几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写字楼。

离开建筑工地后,张波进入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当业务员。这是城市经济发展催生的新行当。
随着市场经济网络的逐步下沉,全国中小企业户数持续增长,它们最主要的经营风险就是资金周转。数额一般不大,一两万到20万元之间,但需求很频繁。如果从银行借贷,不仅需要复杂繁琐的手续,而且传统银行服务的对象是国企或者大公司,中小企业被拒绝的概率很大。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2011年到2017年,全国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贷款余额的增长都超过三倍。

《创业时代》剧照
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员是一个入行门槛不高,但更接近“上班族”的行业。业务员需要每天穿着整齐,去拜会各种中小企业主,收入主要来自拉到贷款客户后的签单提成。而能否拉来客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交能力和人脉资源,“能说会道、会拉关系”的张波似乎天生适合这个职位。
张波的前同事刘东告诉本刊记者,一起共事时自己曾遇到难缠的客户,无论如何说服不了。张波接手后,查资料发现客户也是长寿人,于是在饭桌上特地点了一道老家特色的活水豆腐,从长寿区的特产聊起,聊到后面甚至和客户扯出了远亲关系,当晚就把单子拿下了。
“能干、肯干,很精明,是个赚钱欲望很强的人。”刘东对本刊记者回忆张波。 他记得在公司内,张波并不算特别合群,有时会拒绝同事打牌、唱歌的邀约,“但如果跟他说有单子签,他跑得最快,午饭都不吃,拎个包就去了”。

《宽松世代又如何》剧照
刘东的儿子出生后,张波主动开车到小区楼下,给刘东300块钱,“他说不知道孩子穿多大的衣服,让我自己给小孩买,然后说自己交通违规了,要借我的驾照去扣分”。
同样在葛兰镇长大的何彦也对张波有相似的印象:有事业心、头脑活络,还很有野心。初中毕业后,何彦到广州开货车,给一家大公司拉货。2017年底,在朋友组织的一个烧烤局上,何彦第一次认识了“老乡”张波。朋友介绍张波“在重庆上班,娶了个城里媳妇儿”。
何彦有些羡慕,他和一个老乡在广州的城中村租了一个房间,睡上下铺,拉货时常常要轮流出夜车,在广州湿热的天气里,即使只穿一件背心,也忍不住汗流浃背。而张波是饭桌上仅有的两个“上班族”之一,衣着体面,表现得外向、聪明,言谈间会蹦出一两个何彦听不懂也不好意思追问的高级词。

《猎场》剧照
在小镇青年的眼里,张波已经成功离开农村,在城里扎下根来。但面对真正的“城里人”,张波仍不免表露出自卑。 陈美霖记得,有一次自己表哥从江苏来重庆,家族聚会为表哥接风,席间众人推杯换盏,聊的都是些家长里短。
回家后,张波却发脾气了。陈美霖有些莫名其妙,她事后回想,表哥是江苏一家企业的高管,刚刚被另一家企业“高薪挖走”,两个姐夫分别在中石油和烟草公司工作。不知道席间他们的什么言行,让还是小公司业务员的张波觉得脸上挂不住。
他对陈美霖说:“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我再也不会参加这种聚会了。”
当老板

第一次和何彦见面时,听说何彦在广州跑车,张波就积极地向他打听拉货的事,很快弄懂何彦的工作内容和收入后,张波问他:“为什么不自己搞一个小型运输公司?自己当老板?”
“自己当老板”是张波的梦想。这个梦想起源于何时,或许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在他从乡村去往城市的长路上,在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小额贷业务员过程中,努力去接近的那些中小企业老板们让他感觉到,老板是一种自由体面的城市角色,有远高过工薪族的收入,不受制于他人,生活肆意自由。
或者说,“老板”是一种机会,是这个时代给予出身普通甚至贫寒的年轻人的机会,只要你聪明、努力、头脑活络,就可能“弯道超车”,彻底摆脱城乡差别导致的身份和尊严困境。

2017年8月,结婚后没多久,张波就提出要和朋友合伙开一家小额贷公司,让陈美霖刷信用卡为自己支取3万元,作为他的入股资金。在小额贷款行业摸索了几年,张波有一些人脉积淀,这让他的事业起步很顺利。陈美霖记得,新公司成立后,张波平均每个月能挣2万块左右,最多的一个月挣过6万块。这样的收入已经超过重庆的普通“上班族”。
但张波的生活也在逐渐变化。他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应酬,有时晚上12点多也没回家。以前,他和同事的聚会大多选在商场的火锅店,人均100来块钱。如果回到老家,和镇上朋友的聚会则更加随意。何彦两次见到张波的饭局都是在镇上的露天烧烤店里,闷热的夏夜,男人们喜欢光着膀子,露出文身,抽烟、撸串,大声嚷嚷着喝酒聊天。
但现在张波出入的是“另一个世界”。 他常常向陈美霖情绪高涨地描述高档酒店的模样、在应酬中喝了多么昂贵的酒,言谈间出现各种奢侈品品牌,还给自己买了一条近5000块钱的名牌皮带。
“他好像非常向往有钱人的生活。”陈美霖对本刊记者回忆。 当时她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劝张波早点回家,张波不耐烦地回应,“我不用去拉资源吗?家里的钱从哪里来?”他告诉陈美霖,自己刚结识了几位“做工程的老板”,和他们社交“不能太掉面子”。

汪涛告诉本刊记者,新世纪初的十年是工程建筑行业的黄金年代,只要能拉到工人,“钱是赚不完的,不停地自己找上门来”。即便只是个包工头,也能接到不小的工程。
他记得,2003年北京西站地下停车场扩建时,“好几百万的大工程”,有人主动打电话问他做不做。因为工程量排不开,自己不得不拒绝。虽然这几年的行情大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包工头们早就完成了财富积累,自己也已经给两个儿女在重庆市区购置了大房子。
但对做工程的人来说,要维系住财富的来路,最要紧的是能维护好和开发商、发包方的关系。 “累死累活干了一年,他们决定了你的工程款能不能按时结。必须经常请吃个饭、唱个歌,逢年过节问候一下,这都是套路。”
汪涛说,大部分做工程的小老板也是农民出身,并非挥金如土的人,只是消费习惯在“谈工作”时悄然改变了。“请人吃饭能在街边的小馆子吗?一瓶几百块钱的酒拿得出手吗?别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你能穿着工服去吗?”
张波并不了解“老板”生活的全部。他似乎被眼前所见的奢华生活迷住了,很愿意投身其中。 2018年,他坚持动用家里积蓄,再贷款19万元,买了一辆总价40万元的奔驰,把它当作出入“上流社会”的体面装备。夫妻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陈美霖甚至两三天都见不上张波。
2018年3月,女儿小雪出生。几个月后,陈美霖发现自己再次意外怀孕了。生小雪时的大出血让她后怕,考虑到照顾孩子的经济负担,她原本想流产,但医生提到,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人工流产的方式她无法接受,“好像要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她几次询问张波的意见,张波的回答有些轻飘飘,“都可以,你想生就生下来呗”。
“轻飘飘”,是张波对待孩子一贯的态度。 虽然这段婚姻的基础就是意外怀上的女儿小雪,但直到儿子小洋出生后,陈美霖感觉张波从未表现出作为父亲的热情。他不会换尿布、不会冲奶粉,甚至从来不主动抱孩子。

创业前,他一回家就躲进房间里打游戏、看视频。创业后则大部分时间在外面,每天开着奔驰车出门,直到深夜才回家,有时干脆夜不归宿。前同事刘东也告诉本刊记者,与张波相识的三年里,从未听他主动提起老婆和孩子。每次自己问起,他才会有些敷衍地答上几句,又很快把话题岔开。
2019年3月,刚出生两个月的儿子小洋不断咳嗽,被诊断为严重肺炎,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陈美霖吓哭了,一个人在医院颤抖着签了字。
她记得,住院治疗的一周时间里,张波只来看了孩子两三次,每次只待一两个小时,就以“一会儿要跟客户去吃饭”“我今天要早点回去休息”等理由离开。 有一次,两人一起给小洋喂药,张波抱着孩子,陈美霖俯身把奶瓶递到小洋嘴边时,张波下意识地把身体后仰,拉开彼此的距离。
陈美霖捕捉到了这个细小的动作。2019年4月,小洋出院那天,陈美霖提出和张波好好聊聊,她感觉和丈夫的距离越来越远,希望能通过交流弥补婚姻的裂缝,但张波没有给她机会。

《婚姻故事》剧照
“我们离婚吧。”陈美霖记得他这么说,“我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跟两条平行线一样。你要的是平平淡淡的生活,我要的是大富大贵的日子。”“你知不知道,跟你多待一秒钟我都觉得很痛苦。”
新世界

还没和陈美霖离婚时,张波的朋友圈封面已经换成了与新女友叶诚尘的合影。两人靠在一起,坐在一处景观台地上。照片里的叶诚尘很瘦,皮肤白皙,巴掌脸、尖下巴,穿一件半露肩的灰色薄毛衣,长发略有些凌乱地垂到胸前,是时下流行的时髦都市女郎模样。
刘东第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时问张波:“在哪里找了个小网红?”但陈美霖对叶诚尘了解稍多一点,“实际上更黑、更胖些,穿着满身名牌”。
新女友叶诚尘也是长寿区人,和张波同岁,是重庆一家食品公司财务人员。公司的大股东是她的父亲,她只需要偶尔去公司一趟。
叶诚尘的爷爷曾告诉记者,读书毕业后,家里人觉得女孩子在外工作辛苦,就给她在公司里挂了个职务,“每个月发一些工资,免得孩子到处跑。”何彦记得,自己再次在饭桌上见到张波时,朋友揶揄张波“当了老板,找了个富二代”,张波有些不好意思,推搡着假装要打人。
新女友代表着张波想要进入的“新世界”。女友的父亲是老家人眼里最成功的样本——做建筑工程起家,发展出一个商业版图。 食品公司只是他入股的一家公司,还担任过重庆市长寿区某矿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是老家镇子上“出名的有钱人”。看起来,结识新女友让张波离自己想要的生活圈子越来越近,但实际上,他的麻烦却越来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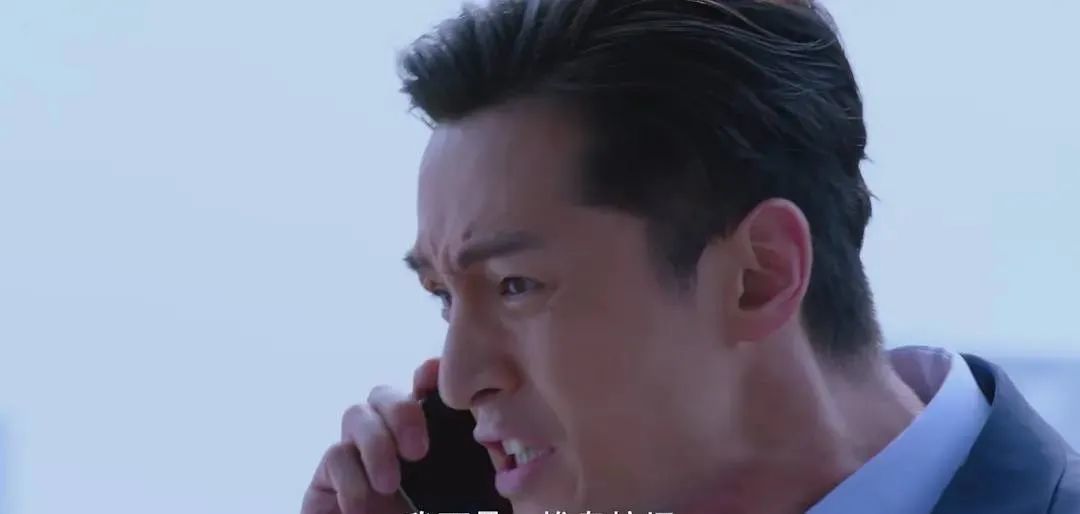
2019年下半年,和叶诚尘确定恋爱关系后,张波像当初对待陈美霖一样,交出了自己的工资卡,却并没有换来女友的信任,他的收入也无法满足女友的开支。刘东记得,张波对自己诉苦,说经济压力变大了许多,几次开口借钱,几百块到上千块不等。
2019年底,张波和合伙人的合作终止,离开了自己创立的小额贷公司。 据说散伙的原因是“张波整天忙着离婚和叶诚尘的事情,把合伙人搞得很烦”,还“吃了一笔公司的钱”。
更大的麻烦是迟迟拿不到手的离婚证。 他想继续和新女友的关系,首先就要和过去斩断联系。张波还未离婚时,新女友就用他的微信号发了一条朋友圈,公开宣示“主权”:“陈美霖,你们现在已经没有关系了,张波最爱的人是我。”
张波也急切地希望用离婚证来证明自己对新感情的忠诚。“恨不得今天提了,明天就去离。” 陈美霖对本刊记者回忆,她不想离婚,想为年幼的孩子维持一个表面上完整的家。但来回纠缠大半年,再加上母亲又查出甲状腺癌晚期,陈美霖心力交瘁,最终同意了离婚。
2020年2月,她和张波签订离婚协议,约定女儿小雪由陈美霖抚养,儿子小洋由张波抚养到6岁后交给陈美霖。张波支付80万元作为补偿,分8年还清。
婚姻结束了,张波获得了奔往“新世界”的自由,杀机怎么还会蔓延到孩子身上?这是这起悲剧中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而且,根据起诉书显示,两人的共谋是从2020年2月,也就是刚离婚那会儿开始的。
或许,在一段以金钱为诱饵和目的的情感关系中,占有和屈服理所当然,永无止境。起诉书显示,即使已经离婚,叶诚尘仍然多次向张波提起,自己和家人都不能接受张波有孩子,否则不会同张波继续发展。
对杀害自己的孩子,张波有过犹豫,但他的迟疑更多来源于动手的恐惧。 陈美霖告诉本刊记者,根据事后恢复的二人聊天记录,叶诚尘第一次提出杀害小雪、小洋时,张波拒绝了。
“他说:‘要干你自己干,我可不干。’两人还谋划过制造车辆意外落水的方法,因为车子没买保险,就放弃了。”随后,叶诚尘多次发微信催促张波作案,张波迟迟没有动静。
2020年6月,张波和叶诚尘分手。9月中旬,张波主动联系叶诚尘和好。为了恢复关系,他交出自己的两个孩子——两人继续通过面谈、微信聊天的方式共谋这起罪行。
坠落
离婚后,孩子是陈美霖全部的生活,她常常和小雪、小洋一起拍各种搞怪的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

《三十而已》剧照
小雪长得和妈妈一样,皮肤白皙,有时扎两个小辫子。她像一个小大人,陈美霖吃饭慢,小雪会站到小椅子上催促她:“妈妈,快点啦,快点啦,要洗碗啦。”外公倒车时,小雪也学着导航喊口令,“倒,倒,好!停啦!”
儿子小洋的性格则大大咧咧,不怕生。他最喜欢陈美霖的爸爸,一见到外公,就张开两只手,摇摇晃晃地走过去,要外公抱。
她学着接受自己的“新生活”——虽然丈夫以如此让人伤心的方式离开,承诺的抚养费也只支付了3万元,但还好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城市,有父母和朋友在身边,单亲妈妈的生活也不那么可怕。 有时,她下班回来,累得靠在沙发上休息,小雪会爬到她的腿上,抱住她的头轻轻拍着念“妈妈乖”。

《恶之花》剧照
10月2日,她接到张波的电话,说要带小雪买衣服,要她把孩子带到锦江华府小区。 这让陈美霖和妈妈有些警惕。
离婚后,每逢周末,陈美霖会带着小雪去和小洋玩,几乎不曾遇见张波。他很少在家,更不要说陪伴孩子。陈美霖的妈妈也提醒,“小雪两岁半了,张波一次都没来看过孩子,怎么突然这么好心。你要小心,他是不是想把孩子卖了”。
但小雪想见父亲。 因为母亲刚坐完月子又怀了弟弟,这个小女孩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外婆家。父母开始闹离婚时,小雪才一岁,她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两岁半时曾经问外婆:“爸爸在哪里?我还不知道爸爸是谁。”
想到这些,陈美霖有些心酸,她同意把小雪送过去,但自己全程陪着。 那一天,张波带着小雪上街,拉着她的手进店里买裙子。晚上回家后,小雪依然很激动。这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陈美霖问她:“你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小雪的回答让人又气又好笑。她毫不犹豫地说:“我想爸爸,我喜欢爸爸!”
11月1日,张波再次联系陈美霖,要把小雪接到锦江华府的家中。陈美霖问小雪:“要不要去爸爸家?”小雪用力点了两次头,回答:“嗯嗯!”
这一次,张波提出让小雪留下来过夜。 “他说:‘陈美霖,算我求求你了,让孩子留下来吧。’”陈美霖对本刊记者回忆,她问小雪:“晚上和弟弟一起住在爸爸家,明天妈妈再来接你,好吗?”小雪很兴奋地同意了。这是陈美霖最后一次见到两个孩子。

图|视觉中国
坠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恋人”张波和叶诚尘在法庭上发生了争执。 陈美霖旁听了整个庭审,她对本刊记者回忆,张波说事发时自己正在与叶诚尘视频,是叶诚尘选择了较为隐蔽的卧室窗户作为动手的地方,随后又用割腕的方式逼迫自己动手,自己被逼急了。
但叶诚尘否认了这一说法。“她说当初谈恋爱是被迫的,因为张波威胁要杀她全家。还说她认为张波对孩子下不去手,割腕是想着张波能知难而退,主动提出分手,‘外面还有十几个男的排队等着我耍朋友呢’。”
(文中刘东、何彦、汪涛为化名。)

 重庆两幼童坠亡事件:最亲密的杀害
重庆两幼童坠亡事件:最亲密的杀害 考高分的他们,为何选择去职高?
考高分的他们,为何选择去职高? 75岁的中国最年长钢管舞者,有11年舞龄
75岁的中国最年长钢管舞者,有11年舞龄 罗康瑞:一个香港人在上海
罗康瑞:一个香港人在上海 西藏军区边防条件日益改善,墨脱迎来首
西藏军区边防条件日益改善,墨脱迎来首 数字人民币发行规模有多大?现金还会存
数字人民币发行规模有多大?现金还会存 “美翻了,我的村”第三季:守望绿水青
“美翻了,我的村”第三季:守望绿水青 学习消防知识 提高安全意识
学习消防知识 提高安全意识
 习近平参观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习近平参观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一见·母亲河 幸福河——总书记的“治河
一见·母亲河 幸福河——总书记的“治河 “大观杯”摄影比赛发奖仪式暨摄影作品
“大观杯”摄影比赛发奖仪式暨摄影作品 重庆:老旧社区变身网红文创新地标
重庆:老旧社区变身网红文创新地标 国庆佳节,他们坚守战位
国庆佳节,他们坚守战位 多彩花灯迎中秋
多彩花灯迎中秋 福建独有,全国罕见!福州夜航龙舟火了
福建独有,全国罕见!福州夜航龙舟火了 安心!暖心!应对突发情况,山东交警随
安心!暖心!应对突发情况,山东交警随 结缘农业八十年
结缘农业八十年 一生为国铸盾 映照百年风云——追记第七
一生为国铸盾 映照百年风云——追记第七 83岁樊锦诗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83岁樊锦诗当选全国道德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