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5日,江西遂川,雩田镇塘背、彭汾村老人们在“互助之家”里拉琴、唱歌。近年来,遂川县采取“政府补一点、社会捐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建立了218个“党建+互助之家”。(视觉中国/图)
在吉林省松原市杨家村,全村三百多名中青年外出打工后,老人们留守家中。51岁的杨家村妇联主席张春玲带头,自2014年组织起22人的志愿者服务队,给60岁以上的老人们收拾屋子、洗被褥、擦玻璃等等。有时候,也帮老人们在园子里做些收割,帮助买些日用品。
志愿者的年纪在25岁到58岁之间,以当地的妇女为主。如果老人是失能、半失能的状况,有事可以随时打电话,让志愿者上门。志愿者服务一个老人按小时计算,村里给予一定的补贴。
这种基于传统乡土社会守望相助的养老方式被称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2021年12月8日,国内首份聚焦这一模式的《中国农村互助养老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由中国老龄协会委托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学与政策研究中心(华北电力大学老龄科研基地),基于2017-2020年对北京、上海、河北等9省市农村互助养老的发展状况实地调研完成。
在报告课题组看来,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有现实的迫切性。根据2020年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0年中国乡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23.8%,比城市高出8.0个百分点。
根据全国老龄办的数据预测,在2020-2050年间,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一直高于城镇。到2035年,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提高到37.7%,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进一步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出城镇13个百分点。
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认为,发布这份报告,就是希望推动社会力量共同关注和推动农村互助养老,“使这项适合中国国情、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养老模式在更大范围内探索实施、落地开花”。
低龄老人提供人力支撑
何谓互助养老?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老龄科研基地负责人刘妮娜认为,常见的抱团养老、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都包括在内,但又不止于此。农村互助养老可以发展有偿服务,只是相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养老院而言,服务价格会比较低。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刘妮娜在报告中总结,“互助养老具有低成本、非营利、多元参与、灵活多样的特点”。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原宜州市),互助养老由政府出资主导,依托当地的老年协会进行。宜州自1989年大量设立养老协会,“基本上每个村都有”,原河池市宜州区老龄办主任韦玉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老龄委启动基层老年协会养老互助服务试点工作,明确将组织实施8个政府购买基层老年协会养老互助服务试点,其中,村级老年协会5个、屯级老年协会3个。
据韦玉娟介绍,宜州区老龄办每年给老年协会拨款两万块,补贴老人活动支出,并聘请年轻一些的、热情的老人,每周打开村里的活动场所,给老人们下棋打牌,聚会聊天。同时,每人根据情况负责2-3个屯,每周到重点关注的老人家里探访,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老年协会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仅有50元补贴,但由于是服务乡民,且当地敬老氛围浓厚,他们也很乐意。
据韦玉娟观察,宜州农村鲜有市场化的养老院,村里的失能老人大都由子女照顾,对需要付费的养老院需求不大。每个乡镇设有敬老院,主要服务没有子女的五保老人。但这些老人除非行动不便,也更愿意居家养老。
韦玉娟总结,当地农村老人更需要的是娱乐、精神慰藉类的活动。她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初一、十五,老年协会邀请村里的老人聚餐,“你拿一点米,我出一点菜”,共同做一桌好菜。饭后老人们一块唱山歌,场面热闹。
而在吉林省松原市的杨家村,在志愿者服务队的尝试后,2017年建起了村级的托老所。据张春玲介绍,托老所硬件设施主要由上级民政部门出资建设,本村自筹五万元。托老所为老年人提供住宿、吃饭、娱乐以及生活照顾服务等,老人每月收费300-500元不等。村医能够免费看些小病,洗发、理发都是免费的。
初期,张春玲担任执行院长,先找村里的妇女们谈话动员,承诺干1小时补贴8元,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她认为,托老所必须找有爱心的人经营,“对待老人像自己父母一样才能做好,要尊老爱幼、品质优良、舍得为老人花钱,没事陪老人唠嗑、讲故事”。
“她是非常积极、对此有热情的人”,刘妮娜认为,正是张春玲这样村里的党员干部,以及低龄健康(准)老人、妇女等群体为互助养老开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
一村一策
另一方面,近些年农村养老服务硬件设施在逐步完善,为互助养老提供了依托。据课题组整理,2012年,民政部开始在全国推广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的农村互助幸福院模式——由政府支持、村级主办、社会参与、互助服务性质的村级老年人公共服务设施。各地也在开始建设幸福大院、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餐桌、托老所等各类硬件设施和配套设备。
农村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在此期间大幅增长。根据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统计,该类设施从2014年的4万个,到2017年达到了8.3万个。
但硬件设施建成后存在利用率低的问题。韦玉娟就提到,广西宜州的农村主要位于山区,大家居住得比较分散,“每天聚在一块供餐、午睡不太现实”,幸福院的日间照料模式因此施展不开。2017年后,政府政策导向逐步由偏重硬件设施建设向互助服务供给转型。
课题组在走访调研了37个农村互助养老典型案例调研后,对中国已开展的农村互助养老现状做了分析。他们将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划分为资金、运营、服务等。
37个典型案例中,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政府、基金会、村集体、抱团共兑等,运营主体包括村两委、老年协会、社工机构和社会企业等,服务内容则涵盖助餐、生活照顾、精神慰藉等,“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要素搭配方式”,刘妮娜介绍。
以资金来源为例,北京市延庆区慈善协会通过承接延庆区民政局委托的“1+1”助老项目,将互助养老覆盖了延庆区15个乡镇。这个项目中,资金源自政府,依托各村助老服务队执行。互助志愿者可以获得一定的资金补贴,给老年人理发1次,补贴10元;助医、助洁、助餐,每次补贴20元,助农1次至少3个小时,补贴100元。
另外一些地方在资金来源上则选择了“抱团共兑”。如浙江省杭州市长命村的抱团养老,每对夫妇支付每月800-1500元不等的费用,用于支付家中请来的厨师、小时工以及园丁的工资。一些地区的老年协会收取会费用于日常互助服务开支。浙江安吉、广西宜州农村老年协会的入会率基本达到100%,会员缴纳会费的比例也超过80%,安吉县会费标准为20-50元/年/人不等,宜州区会费标准为10-20元/年/人不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报告发布会上指出,要研究互助养老的多元性、多样性、个体性。“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一定是一村一策,要贯彻多元理念、差异化发展。”
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在报告中,课题组也总结出互助养老的诸多痛点问题,包括社会认识不足、资金来源单一、服务供给短缺且质量不高等。
目前农村互助养老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主要定位为活跃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临时帮助。在课题组调研的37个农村互助养老典型案例中,开展文化娱乐、上门探望服务的达到100%,但是生活照顾类的仅有70.3%,康复护理类的仅有10.8%。
课题组认为,安全问题是影响因素之一。互助服务缺乏风险防范和纠纷调解机制,一旦在服务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双方权益都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也制约了服务双方参与的积极性。
对于高龄、失能老人照护,刘妮娜建议引入市场化的专业护工,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护理流程。“老年餐桌”服务也建议通过资金补贴,实行规模化、连锁化经营。
但她强调,没有互助养老模式带来对老年人的凝聚、信任网络的建立、低成本服务的供给,市场养老也很难在农村推动发展。她在调研中观察到,农村养老观念不同,对于外来的养老市场资本会有一定排斥,大部分在农村的养老院都由本村或者邻村、邻镇的人员建立,“都是跟本村有一定关系的”,有信任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林宝认为,农村老年人除了生活服务外,作为农业劳动者也需要生产服务,农村互助可以是生产生活领域全方位的互助。
刘妮娜也认同这一点。她在报告中指出,互助养老的意义不仅在于服务,还有参与中的归属、团结与信任——共同体意义。它可以以社会互助带动经济互助,助推农民合作社功能进一步强化。但目前农村互助养老仅仅局限于老年人互助服务,对带动经济互助合作的认识不够。
华北电力大学、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自2019开始举办创新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学术研讨会。在首届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曾发言表示,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要发展互助式养老,近年来在政府推动和社会参与之下互助养老广泛开展,说明互助养老是具有发展意义的。但是,互助养老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养老模式,未来应该如何发展,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
此次发布的报告建议,“加强规范指导,提高互助养老的服务质量”,要明确农村互助养老的定位、内容和路径,以及各级各类互助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刘妮娜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让各类互助组织充分发展起来,也才能对其进行更为有效的监管和评估。比如老年人互助会、抱团养老能否在民政部门登记和备案,提供照护类服务的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是否可以申请政府建设补贴、床位补贴、水电优惠等。

 张一鸣半只脚踏进元宇宙
张一鸣半只脚踏进元宇宙 打好夏粮丰收仗——我国全力以赴保障粮
打好夏粮丰收仗——我国全力以赴保障粮 互助养老:更适合农村的养老方案?
互助养老:更适合农村的养老方案? 成都大运会奖牌“蓉光”全球首发亮相
成都大运会奖牌“蓉光”全球首发亮相 土耳其发生多车连环相撞事故 致30人受伤
土耳其发生多车连环相撞事故 致30人受伤 开学“发糖”!济南三中“心灵有约”邀
开学“发糖”!济南三中“心灵有约”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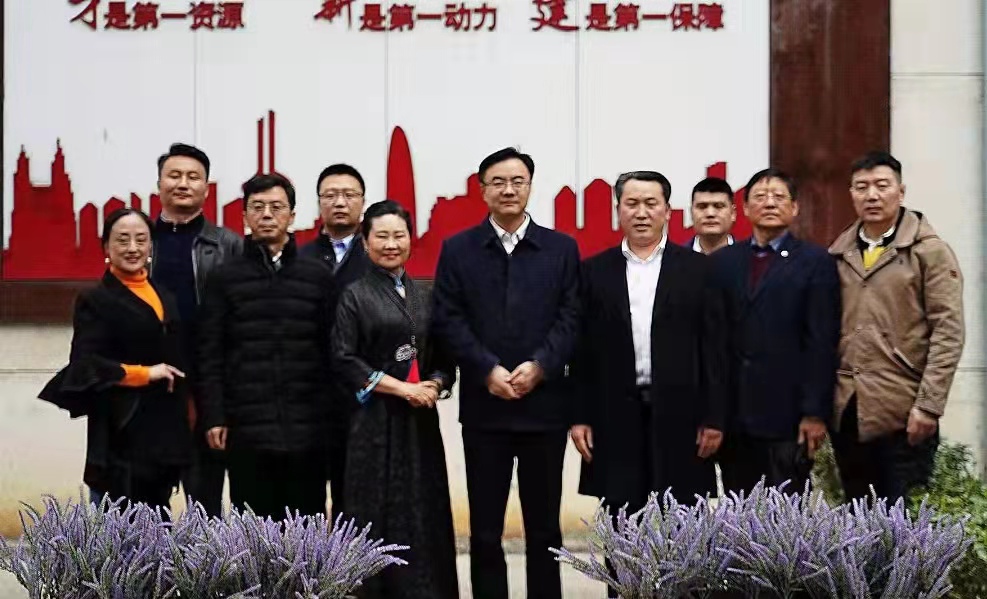 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局领导莅临泉水联盟
济南市民营经济发展局领导莅临泉水联盟 全国一等奖!济南三中崔文涵、周经
全国一等奖!济南三中崔文涵、周经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圆满闭幕 习近平李克
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圆满闭幕 习近平李克 开闭幕式团队:闭幕式依旧“简约” 将致
开闭幕式团队:闭幕式依旧“简约” 将致 春暖花开景宜人
春暖花开景宜人 开学遇上冬奥 我们一起加油!
开学遇上冬奥 我们一起加油! 红红火火迎新春 广西军营“年味”别样浓
红红火火迎新春 广西军营“年味”别样浓 冬雨滋润腊梅见美景
冬雨滋润腊梅见美景 第四十八届哈尔滨冰灯艺术游园会免费迎
第四十八届哈尔滨冰灯艺术游园会免费迎 红火迎新年
红火迎新年 冬奥的诞生:一种更为彻底的对于极限的
冬奥的诞生:一种更为彻底的对于极限的 国士的爱情:与妻子肝胆相照60年,从未
国士的爱情:与妻子肝胆相照60年,从未 宝清县:制作彩色图案“走马灯”助
宝清县:制作彩色图案“走马灯”助 这个不信命的女孩,改变了更多女孩的命
这个不信命的女孩,改变了更多女孩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