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个2020年,在线教育行业都在疯狂融资、扩张、招人、打仗,他们给应届生开出高薪,用9.9元的低价课吸引家长,把广告打到电梯、地铁站、综艺节目甚至春晚,但当监管如风暴般来临后,泡沫一个个接连破碎,一些人被狠狠抛下,他们才开始反思:这真的是教育吗?
“家长究竟会怎么看我呢,他心里会不会特别瞧不起我这个老师?”当陈珏打给家长的电话又一次被挂断时,她心里十分难过。
陈珏是某头部教育机构的小学英语老师,即便已经入行三年,她还是难以忍受这种尴尬与委屈。她放下手机环顾四周,三十多位老师在低头打电话,她没时间继续难过,很快拨通了下一个号码。耳边实在嘈杂,为了让另一边的家长听清,她不断放大音量,直到电话再一次被匆忙挂断。
教室失去秩序,陈珏的情绪也接近失控。抬眼,已经晚上十点。每年的四月与十一月,所有小学段老师在下课时间都会被集中在一间空教室,为了暑期与寒假的续班打电话。
168个号码,家长们汇集在陈珏的通讯录里。整个四月,陈珏将没有时间备新课,所有空闲都消磨在通话任务中。第一轮才刚刚开始,按照领导的计划,三天时间内,陈珏至少得将所有号码“熟悉”一遍。
陈珏无法反抗,因为或明或暗的比较无处不在。最直观的是内部续班率排行榜,每隔半天,数据就刷新一次,并以出乎陈珏意料的速度提升,直至无法再突破的顶点。“最后会有老师续班率到达100%,公告上就这样写着,不知真假。”
续班天花板在飙升,要求也变得越来越严苛。达标率从85%上调到90%,陈珏从来都是完不成的那一个。“我一般在80%左右,完不成,也不想完成。”
但至少在计数考核上,没有老师愿意输。“很简单,任务没达成要发红包。”领导对通话次数的要求已经具体到小时为单位,一个小时内,如果没有打满5个电话,老师将面临发50元红包的处罚。下班后,陈珏需要将所有的通话记录截图发至大群中,有专人负责统计时长与次数,最多的一次,她发了200元红包。
正常情况下,晚十点半后,老师不再继续打电话给家长。她决定拨打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电话刚响起,家长清楚来意后,直接告诉陈珏:“老师,你知道吗,我很反感你这样。”
挂掉电话,陈珏默然。就在几小时前,她还是孩子的老师,现在,她更多承认自己是“话务员”。黑色的手机屏幕像一把刀,将她割裂开,“我的人格破碎了”。

被卷入营销大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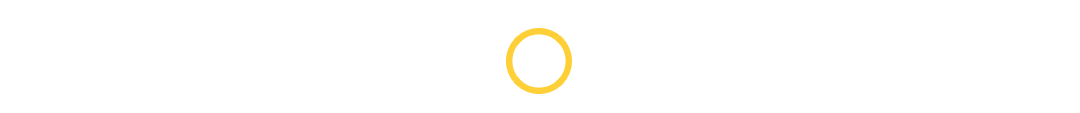
从2018年进入教培行业,陈珏的3年恰好赶上了教育机构的扩张期,疫情尤其加速了在线教育的发展进程。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20年3月,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4.23亿,较2018年底增长2.22亿,增加了110%。
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K12教育抢先吃到红利,资本如潮水般涌入。2020年3月,猿辅导完成10亿美元F轮融资,投后估值约为78亿美元。此后,作业帮、掌门教育等机构先后启动新一轮巨额融资。《商业数据派》根据公开信息统计,2020年1月-11月末,在线教育行业披露的融资金额共计约388亿元,较2019年同期的108.75亿元,增长了256.78%。高途集团董事长陈向东透露:“2020 年全球教育投资大概有80%都流向了中国,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难以想象的。”
张平发现,不知何时,公司的广告开始无孔不入。“视频广告、公交站牌、大楼广告牌,哪哪都是。”他就职于一家知名在线教育机构,这家机构在行业内已深耕多年。“刚入职的时候,几乎没有广告投放,广告牌都少见,那时候我们的理念是‘用口碑召来学生’。”

▲ 郎平和中国女排代言在线教育产品现身上海。图/视觉中国
但转变很快发生:靠口碑太慢,靠广告才快。张平和身边的同事私下调侃,“公司应该把价值观改成‘拥抱变化’,或许就不会那么尴尬。”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统计,2020年电梯LCD刊例花费TOP20品牌占电梯LCD总体比重的38.8%。其中在线教育品牌斑马AI课和猿辅导首次冲入榜单,且占据了第一和第三的位置,广告投入增势迅猛。猿辅导和学而思网校的广告还打到了2021年央视春晚,在线教育各大公司也是字节跳动、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最重要的广告主。
所有教育机构都在尽可能抢占家长注意力,而这种需求也被精准量化为老师们的工作量。去年临近暑期前,公司要求张平兼职市内某片区所有小学的地推工作。他揣着一摞机构福利——一些机构自出、但不附赠答案的免费试题卷,掐准放学时间,来到小学门口。
这或许是张平从小到大最受长辈欢迎的时刻,在子女教育面前,这种欢迎真诚而迫切,他手中的试卷引来大爷大妈举手疯抢。“和发传单不一样,传单可能会发不出去,但我们不愁,我更多的工作是维护秩序。”
“试卷上没有答案,想要知道自家孩子分数,必须扫码。”张平道出其中套路。实际上,机构并非在意这样的地推能获客多少,“重要的是刷脸,让别人有印象,毕竟现在所有的机构都在打广告”。
但额外的地推工作让张平十分疲劳。除此之外,作为主讲老师,他还需要录制视频、运营社群。“我以为我会是一个教书匠,但机构给我的定位,和我自己的定位,有明显的偏差。”
被卷入这场营销与抢人大战的,还有不计其数的辅导老师。去年疫情期间,李依依投递了某线上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岗。在面试时,人事直接告诉她:“这份工作不仅是辅导老师,更重要的是,需要你接受销售性质。”他停顿了会,“甚至销售会占工作的一大部分”。
公司占据了郑州某写字楼四层的面积,“全部都是打电话的人,全部”。李依依第一次走进办公室,在这里,所有人的面孔模糊,头戴式耳机或许是他们唯一的身份标识。“声音非常非常大,很躁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但通话对面的家长往往感受不到,“因为耳机的降噪效果很好,据说很贵”。
入职后,李依依成功被包装为一名211毕业的老师,她需要完成为期一周的电话考核,才能正式成为一名辅导老师,“否则将面临第二期考核”。李依依拿到了接近130个手机号码,这些号码来自于曾经购买机构9.9元试听课的家长。“一直打,一直打,打到关死。”所谓关死,即电话、微信以及所有联系方式彻底拉黑。
“但我们依旧有办法,换一个电话,用同事电话继续打,打到所有电话打不通为止。”公司每天凌晨12点会统计业绩,在小组竞争的压力下,李依依从未在晚上12点前离开公司。
一周考核的高压,令所有新人都无法喘息,“忙到凌晨一两点都是常态了”。灯火通明的公司楼下,摸出规律的滴滴司机正等待着这些年轻人。一次闲聊时,滴滴司机告诉李依依,大部分女生在那段时间下班后,坐上车就开始哭,“上来一个哭一个”。这样的压力下,公司每天都有新人,“组长告诉我,离职率大概有60%”。
点对点的电话、点对线的地推、点对面的广告,教育机构开始铺设一张牢牢的蛛网。但在蛛网越收越密的同时,捕获“家长”的成本也水涨船高。根据投中网结合财报与东方证券的调研数据,自2019年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跟谁学的获客成本正在逐步上升,最低时只有400元左右,但到了2020年第一季度,这一数据却飞涨至1000元左右。
不到一周,李依依提前脱颖而出,成为一期考核的销冠,成交35单。她认为这张网简直可以称得上天衣无缝,“所有你能想象到的问题,我们都有应对方法”。例如家长认为课程太贵,李依依会将4000元一科的正价课均摊在每一个课时上;如果有家长说孩子学习忙、没时间,“那我们有无限次数的免费回放”。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专访时曾表示,“校外线上培训机构普遍通过融资进行资本运营,但过于逐利,一些线上培训机构为了获取客源,不把钱用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刀刃上,在各大媒体上铺天盖地地做广告,营造所有孩子都需要参加培训的氛围,加重家长的焦虑。”

▲ 培训机构推销。图 / 电视剧《小舍得》
陈珏用《红楼梦》贾府类比现在的教培行业。她认为探春所说的话,相当尖锐且精辟地指出教培行业的问题所在:“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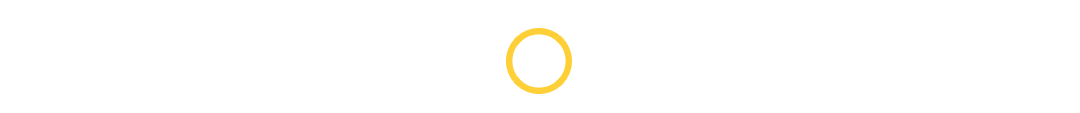
疯狂招来了监管。
5月21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自此之后,教培行业一直在关注“双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政策细则的出台和落地。
许多教育机构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资本已经迅速退潮。美东时间5月21日,美股在线教育板块集体下挫,截至当日收盘,好未来跌幅超10%、新东方跌幅超5%、高途跌幅超10%。如今短短两个月不到,好未来市值蒸发了59%,新东方市值蒸发了47%,高途市值也蒸发了48%。
但这些头部教育机构有的已经提前嗅到了风声。主讲老师张心蕾所在机构,在三个月前已经有所动作。“当时让我们集体补交了教师资格证,也进行了内部自查。”机构特别强调,不允许虚构教师资格经历,“现在只有缴纳社保的经历,才算真正的教师经验,实习和创业都不算。”这样一扣除,张心蕾过去的从业资历整整减少了三年。
除此之外,机构内部出台了一本宣传内容规避手册,调整过去例如“最强王者”“解题达人”等网红风宣传语。“不让我们的PPT内出现最、第一等词汇,所有的教研系统都被过了一遍,敏感词全被改掉。”张心蕾发现,机构已经取消了过去宣传语中对教师毕业于清北的强调,“尽管我们团队大部分的确清北毕业,但现在不可以说了。”
教育机构开始急剧下坠。狂风呼啸,一些附着在边缘的年轻人被抖落下来。
徐之言在六月初被劝退了。她从五月下旬进入某家教育机构,担任辅导老师。一个月不到,主管明确告诉她,“公司留不住人,就算你非要留下,也会以其他方式让你离开”。
实际上这在徐之言刚入职时便已有了苗头。“我们入职前有一个训练营,150人左右,主管对我说往常的淘汰率是10%。”最后,徐之言发现只留下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二三十人。“有人猜测公司应该是担心招生困难,不需要我们这么多人了。”
应届生柳戈也在6月的一个晚上收到了已经签约的教育机构电话,人事讲述了机构目前面临的种种压力与困难,最后委婉告知她:“解约吧。”
已经准备好入职的柳戈,不久前刚在机构附近租下房子。突然的解约让她措手不及,毕业、转租、重新找工作,夹在校园与社会中间,她倍感无力。“过了几天,人事又打电话来,说可以安排个岗位给我,我实在不想折腾,担心又找个理由随便把我开了。”
留存下来的人也开始焦虑。资本遇冷,已经扩张为庞然大物的教育机构,只得猛然收缩。而这些压力传导到个体身上,不再是一个冷颤那么简单。
徐之言的进出时间恰好与教育机构监管风波相遇。“短短一个月,我已经能感觉到一些上面的压力。”她日常最晚十一点半解决完所有工作,但基本凌晨一两点才能离开公司。“总部要求我们一点才能散。但我们忙完工作实在是没事了,就在公司聊天,聊到下班放人为止。”
就算是主讲老师陈珏,也接到了薪资结构调整的通知。“综合算下来,税后每个月平均少了2000。”机构通过增设底薪、调高课时费以及调低绩效费,实际变相降薪。陈珏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基础课酬和绩效,比例各占一半,“其他看似增加了,但我现在的绩效再也没有高于3000元,过去从来没有低于5000元的时候。”
“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前,数学组老师第一批爆炸了,还是他们比较会算。不少人私下吐槽,也有人选择辞职。”陈珏说。
但让陈珏奇怪的是,学生学费提高了。在机构续课三四年的老家长向陈珏吐槽,学费一年比一年高。“他有两个孩子,分别报名英语和数学,去年加起来7000元左右,今年已经涨到了8800元。”
而现在,陈珏的工作量又被加大了。过去机构满班26人,现在扩容至30人满班。“机构要赚钱,但我的注意力有限,没有办法分给这么多的孩子。”
泡沫逐个破碎,教育机构“教育”缺位的问题浮现出来。一些人发现,当教育机构资本化运营,一路营销、拉人、圈钱的背后,或许早已淡化和“教育”的联系。
当李依依终于熬过考核,成为一名长期班辅导老师,却发现一切并没有好转。“我们的课后答疑解惑,甚至与学生的所有接触,还是为了续报,为了钱。”
“辅导老师实际就是24小时销售+客服。你到底是想做老师,还是想做销售,一切凭借道德感。”徐之言在试用期间,只能拿到5500元的保底工资,“但里头工作稍微久一点的员工,工资有两三万,这个绩效绝对不是单纯做辅导老师可以拿到的。”徐之言告诉每日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多将自己看作销售。
徐之言的道德认知,也在这短短数十天内“被彻底摧毁了”。为了引导老人给孩子报班,“同事竟然让对方借钱,甚至贷款。”更让徐之言不可思议的是,机构竟然将此作为正面教材宣传,要求其他同事学习。
陈珏的教学同样没有受到机构足够的尊重。去年9月,刚刚入职这家教育机构两天后,陈珏被告知要接手8个班的课程,“这8个班级的课程内容我一点都不知道”。尽管已经不是新老师,学生群体、课程体系以及教学风格的变化,依旧让陈珏措手不及。
在上完第一节课后,陈珏崩溃了。“从没有上过这样差的课堂。”由于缺少培训,加之排课时间紧张,陈珏匆匆上岗。“后来我自己都发现,这里对教学抓的不严。同样是课程审核,我在上一家需要花费90%以上的用心程度,在这里只需要50%。”
此外,机构要求陈珏每周固定提交家长反馈。“原来一周是30%,现在上升到40%。”这也意味着,陈珏将近200人的班级,她至少需要完成70至80位的家长反馈。“这种反馈还比较严格,如果家长只是说一句谢谢老师或者收到,这都是无效反馈。”领导要求陈珏的反馈截图必须展现与家长的交谈内容,“要有来有回”,由此也耗费了陈珏大量时间,“不仅是下班时间,我双休日还要专门空出一天负责这件事。”

▲ 图 / 视觉中国

坠落中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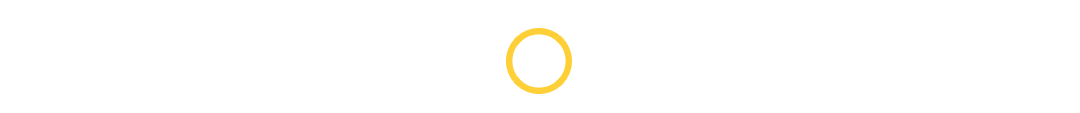
校外培训楼起楼塌,快得像一条抛物线。泡沫涌起时,无论是主讲还是辅导老师,都曾是被机构疯狂争抢的“香饽饽”,而在急剧坠落后,他们又被狠狠抛下。
2020/21财年,好未来员工增加了25643人。高途课堂2017年成立时,公司只有7个人,3年时间就已经发展到13000人,仅2020年就增加了16135人,去年9月还宣称要再招聘1万多名高校毕业生。猿辅导只是成都分公司,员工人数就超过2000人。有机构不惜重金挖走公立校老师,即便是应届毕业生,进入教培机构的起步薪资也比大部分其他行业高出一大截,在高校宣讲会上,“成为名师年薪百万”的标语刺激着每一个毕业生。
教育培训行业如此火爆,根本原因还是来钱太快、太容易了,不管是投资机构的钱,还是家长的钱,都让行业愈加疯狂,并逐步走向失控。
裹挟在行业沉浮间,没有人耗费时间与得失计较,毕竟无论是理想、还是金钱,失去支撑的教育机构,都再也给不了了。

▲ 图 / 视觉中国
徐之言选择教育机构的原因很简单,“钱多”。她所在的二线省会城市工资普遍不高,“在机构工资五千多,努力一下,每个月大概一万不是问题”。如今被仓促辞退,她只能另寻出路。
李依依出于教师理想来到这里,却更直观地感受到职业落差感。作为辅导老师,经常有家长在深夜甚至凌晨,发微信让李依依解答疑问。尽管李依依强调现在是自己的下班时间,家长却反复对她重申教育机构的“服务”意识。“他们或许把我当成一个机器人。”时间长了,李依依对学生的反馈更多出于完成任务的心态。“说实话,早就没有爱的初心了,我甚至有些怕他们找上我。”
对辅导老师而言,学历是她们成为主讲老师的硬性门槛。过去她们认为,辅导老师或许是一种曲线救国道路,是由教育边缘逐渐进入核心的捷径。但机构和家长也许从未将她们看作“老师”,尊严与认同极少出现在她们身上。“我们只是一片可有可无的绿叶。”徐之言说。
但矛盾的是,李依依甚至没有教师资格证。究竟是教育机构给了她机会,还是磨灭了她所有的幻想,她也无法判断。
每年为期两个月的电话销售,总能将陈珏拉回现实,提醒她无非是一个工具。“这里没有所谓的老员工。”陈珏心里知道,没有人想在这里长久。
但教育机构从来不缺人。“因为工资高,很多人愿意为了钱抛弃底线,比如让家长分期贷款买课。”徐之言称,“我厌恶这样的行业风气,但是钱多,短期来看,我还是会做。”
一批又一批的人进出换血,行业的浮躁与喧嚣终究令她们成为教育焦虑的推动者。
徐之言会将学生的小小漏洞和问题无限扩大,“只是为了业绩”。即便是张心蕾这样的高学历主讲老师,在面临续班压力时,也会隐晦暗示家长知识连贯的重要性。“我会放大这个部分,如果不报班的话,学生可能就掌握不到这个知识点。”但实际上,公立学校同样会有这种衔接,“因为这本身就是课内的练习,没有拓展”。
这同样也是陈珏所认为的哄骗。“我告诉家长,我们的课程有衔接性,孩子暑假不学习,秋季就跟不上了。” 部分家长听后非常焦虑,但陈珏告诉每日人物,实际上没有这么可怕,反而续班后的教师变更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不过出现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老师的调换不由我做主。”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续班。“只要钱还在,这种焦虑不可能消失。”
目前,监管的余波仍未停下,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7月2日,北京市教委宣布,各区教委将组织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学生的托管服务,该服务主要提供学习场所,如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等,但并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会适当收取费用。消息一出,“取消寒暑假”的话题立刻冲上了热搜。
陈珏看到消息后,发了一条朋友圈,直言“可怕”。她所在的教育机构本来打算将学生暑期课程集体提前至7月,“但后来发现可操作性不大,毕竟学生的课太多了,时间根本安排不过来。”陈珏向家长们转达了机构的意思,但只有不到10位家长同意调课,计划也就此作罢。
风暴还将持续多久,陈珏已经麻木,她已经决定辞职,“我很爱教育这一行,但我还像个老师吗?”
关于辞职后去哪,陈珏很迷茫。她思考过是否要利用英语专长从事外贸商务,但权衡后发现,跨行颇有风险。“三年的教师经验,除了教学技能,我什么都不会。”
在短暂接触、继而退出教育机构后,徐之言表示“有点恶心”。“我不会放弃教育行业,但绝对不会去教育机构,我选择考编。”
张平已经开始创业,自己开办教育机构,全权负责招生、上课与售后。他尽力降低家长的焦虑感,“家长凭借口碑来这里,我也觉得赚多少钱无所谓,养活自己就好。”陈珏大概率还是会去公立校,过去她认为公立校缺乏活力,但现在这种想法有所转变。“也许我可以将我自己的想法注入课堂。”不过陈珏的职业选择终究是窄了,“感觉这不是一件好事”。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乡村振兴中的科技特派员曹海青:脚下的
乡村振兴中的科技特派员曹海青:脚下的 澳近八千民众请愿引进中国新冠疫苗
澳近八千民众请愿引进中国新冠疫苗 当教培风暴来临 老师们决定下车
当教培风暴来临 老师们决定下车 中国参赛队包揽“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
中国参赛队包揽“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
“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  “一盔一带”安全知识进课堂
“一盔一带”安全知识进课堂 同心协力 守护生命——澳门特区抗疫记事
同心协力 守护生命——澳门特区抗疫记事 东京残奥会-田径男子100米T36级:邓培程
东京残奥会-田径男子100米T36级:邓培程
 山东省第十二届“十佳兵妈妈”颁奖会在
山东省第十二届“十佳兵妈妈”颁奖会在 习近平参观“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党和
习近平参观“友好往来 命运与共——党和 福建独有,全国罕见!福州夜航龙舟火了
福建独有,全国罕见!福州夜航龙舟火了 安心!暖心!应对突发情况,山东交警随
安心!暖心!应对突发情况,山东交警随 “亲情沂蒙·多彩临沂”主题活动成功在
“亲情沂蒙·多彩临沂”主题活动成功在 山东郯城:春雨滋润 腊梅娇艳
山东郯城:春雨滋润 腊梅娇艳 清明将至 缅怀先烈
清明将至 缅怀先烈 山东郯城:年关集市好红火 请福纳福福满
山东郯城:年关集市好红火 请福纳福福满 毛泽东衡山算命
毛泽东衡山算命 470亿“板蓝根大王”离世:人这一辈子,
470亿“板蓝根大王”离世:人这一辈子, 马学虎:奉养四亲为兄捐髓诠释德孝之美
马学虎:奉养四亲为兄捐髓诠释德孝之美